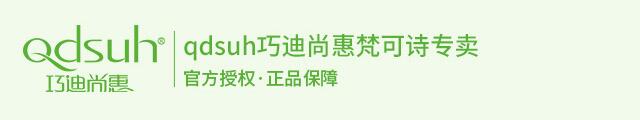陆贽,字敬舆。吴郡嘉兴人,唐代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政论家。773年中进士。唐德宗即位后由监察御史召为翰林学士。783年(建中四年),朱泚叛乱,陆贽随德宗奔奉天,起草诏书,情词恳切,虽武夫悍卒,读之无不挥涕感动。其为相时,指陈弊政,废除苛税。执政期间,公忠体国,励精图治,富远见卓识。在唐王朝面临崩溃的形势下,直陈时弊,筹划大计,为朝廷谋划善策。对德宗忠言极谏,建议皇帝了解下情,广开言路,纳言改过,轻徭薄赋,任贤黜恶,储粮备边,消弭战争。由于他善于预见,措施得宜,力挽危局,唐王朝摇摇欲坠之局面始得以转危为安。关于陆贽的治国思想,可从以下苦干方面见之:
一曰治乱由人,不在天命。唐经安史之乱,藩镇割据,山河破碎,到德宗时已然 “四海骚然,靡有宁处”。泾原兵变后,长安失守,国难益重。但唐德宗在分析原因时却说:“此亦天命,非由人事。”针对德宗的这种“国家兴衰皆由天命”的托辞,陆贽指出“天视自我人视,天听自我人听,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,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”,得出了“天命在人”的结论。并说:“人事治而天降乱,未之有也;人事乱而天降康,亦未之有也。”说明了治乱由人,不在天命。陆贽同时还辩证地分析了“治”“乱”之间的关系。认为“理(治)或生乱,乱或资理,有以无难而失守,有以多难而兴邦”,他劝诫唐德宗“其资理兴邦之业,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”。不要忧虑“乱”,不要害怕“厄运”,只要“勤励不息,足致升平,岂止荡涤妖氛,旋复宫阙”。陆贽的这种反天命、重人事的进步历史观,构成了他治国思想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。
二曰理乱之本,系于人心。安史乱后,时“海内波摇,兆庶云扰”,“人心惊疑,如居风涛,汹汹靡定”,陆贽在“民为邦本,本固邦宁”的传统儒家思想基础上,提出“立国之本,在乎得众”、“得众则得国,失众则失国”、“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,则天下固不治”。陆贽认为:“臣谓当今急务,在于审查群情,若群情之所甚欲者,陛下先行之。所甚恶者,陛下先去之。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,自古及今未之有也。夫理乱之本,系于人心。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,在危难向背之际,人之所归则植,人之所去则倾,陛下安可不审查群情,同其欲恶,使亿兆同趣,以靖邦家乎?”又说:“舟即君道,水即人情,舟顺水之道乃浮,违则没,君得人情乃固,失则危。”作为贤明君主必须要使“其欲从天下之心,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”、“扫求利之法,务息人之术”。贞元八年(792年)河南、河北、江、淮、荆、襄、陈、许等四十余州发生水灾,陆贽劝德宗给予抚恤,并说:“所费者财用,所收者人心,苟不失人,何忧乏用。”他还要求政府“均节赋税”以轻民负。
三曰立国之权,居重驭轻。安史之乱后,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演愈烈,“假四,僭帝号者二,其他顾瞻怀贰,不可悉数”。泾原兵变后,京畿地区也为割据势力所控制。节度使可以“自置文武将吏,私贡赋”,可以大量召募军队,拥有很大权力,官爵、甲兵、租赋、刑杀,皆自决定,“天子不能制”。陆贽吸取了西汉贾谊在《治安策》中所阐述的加强皇权集权的思想,指出:“立国之安危在势。”认为“立国之权,在审轻重,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,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,臂使指,小大适称而不悖”。这就必须要采用强干弱枝之术。加强皇权实力,削弱地方势力,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,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。他告诫唐德宗要“追鉴往事”,并申明:“蓄威以昭德,偏废则危;居重以驭轻,倒持则悖。”因而提出了“修偏废之柄以靖人,复倒持之权以固国”的方针。要求采取一些具体措施,加强关中实力以巩固皇权,逐渐削弱藩镇势力,以便后剪除“凶逆”。
四曰求才贵广,考课贵精。陆贽认为人才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问题。而当时昏庸的唐德宗既不能求贤任能,又缺乏知人之明,“累叹乏才,惘然恍见于色”。针对唐德宗的用人弊病,指出:“朝之乏人,其患有七”:,人才之进用与否不由人才是否合适为准,而由推荐人才的宰相是否受到皇帝的宠信;第二,听信谗言而不加以任用;第三,求全责备,标准太高;第四,对于有“过错”的人,因痛恨太甚而不复用;第五,考察不当,只看表面,不看本质;第六,根据一个人一言一事来决定用与否,不是地看一个人;第七,援引旧例使用朝官阙员,而有才干的人不得升迁。为此他提出了“求才贵广,考课贵精”的重要原则。所谓“求才贵广”就是要求广泛地选拔人才,使人“各举所知”,不仅宰相可以推选官吏,而且台省长官也可以荐举贤能。认为“唯广求才之路,使贤者各以汇征,启至公之门,令职司皆得自达”,才能通过更多渠道得到更多人才。要像武则天那样:“弘委任之意,开汲引大门,进用不疑,求访无倦,非但人得荐士,亦许自举其才。”他反对对人才吹毛求疵,求全责备:“凡今将吏,岂得尽无疵瑕”,认为“人之才行,自古罕全,苟有所长,必有所短。若录长补短,则天下无不用之人。责短舍长,则天下无不弃之士”。他反对“以一言忤犯,一事过差,遂从弃捐”,认为这是造成“乏才”的原因之一。所谓“考课贵精”就是“按名责实”,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考核。陆贽提出了具体的“八计听吏治”,一计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;二计视垦田盈缩以稽本末;三计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;四计视按籍烦简以稽听断;五计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;六计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;七计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;八计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。他认为“才如负焉,唯在所授,授逾其力则踣,授当其力则行”。必须使其才干和所授之官相一致,如果委非所任,处非所宜,就会使器大者不能人尽其才,才小者不能承担重任。 为使奖惩分明、升降得当,在考课基础上陆贽还进一步提出了核才取吏“三术”:“一曰拔擢以旌其异能,二曰黜罢以纠其失职,三曰序进以谨其守常。”这样才能使有政治才能的人得到重用,使庸碌无能、尸位素餐的人受到贬斥,从而使吏治清明,提高官僚机构的工作效率。
五曰广开言路,改过求治。陆贽上书唐德宗,力陈要“广咨访之路,开谏诤之门,通雍郁之情,宏采拔之道”;要召见群臣“备询祸乱之由,各使极言得失,不能当耳目闭塞的孤家寡人”;并进一步指出 “以一人之所览,而欲穷宇宙之变态”是不可能的,只有虚受广纳,勤与接下,“总天下之智以为聪明,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”;陆贽认为要使谏路畅通,必须克服堵塞谏路的“九弊”,其中包括君主“六弊”:好胜人,耻闻过,骋辩给,眩聪明,厉威严,恣强愎。臣下“三弊”:谄谀,顾望,畏懦。指出,上好胜就嫉恨直谏,这样下边谄谀的人就顺情说好话,而真实情况就难以上达;骋辩给就必然不让人把话说完就给顶回去;炫聪明就必然自以为是地加以猜测而怀疑别人欺诈,这样顾望的人便不敢多说话,而一些有深刻道理的见解就不能尽言;厉威严就一定不能和颜悦色地待人接物,恣强愎就一定不能承认自己的过错而接受劝告,这样下边畏懦的人避免进言得罪。所以为君者必须“以求过为急,以能改过为善,以得闻其过为明”。
史传陆贽为相期间,户部侍郎、判度支裴延龄以谄佞德宗受信用,“天下嫉之如仇”。陆贽仗义执言,多次上书参奏裴延龄的罪行。然而德宗却信用奸臣,不听忠言,于贞元十年罢陆贽知政事,为太子宾客。贞元十一年春复贬忠州别驾,陆贽谪居僻地,仍心念黎民,因当地气候恶劣,疾疫流行,遂编录《陆氏集验方》50卷,供人们治病使用。唐顺宗即位后,下诏召还陆贽,诏未至而贽已逝矣。
陆贽的治国理政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《新唐书》的论赞中说他的思想“可为后世法”。司马光非常推崇陆贽,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引用陆贽的议论达三十九篇之多,长者近千言,基本上把《陆宣公文集》的主要内容都概括了。像这样连篇累牍地记录一个人的政治主张,在《资治通鉴》中是罕见的,可见陆贽言论“资治”作用之大。苏轼则说陆贽“才本王佐,学为帝师”,“论深切于事情”,“智如子房而文则过,辩如贾谊而术不疏,上以格君心之非,下以通天下之志……使德宗尽用其言,则贞观可得而复”。并把陆贽的奏议文集进呈给宋哲宗说:“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”,“圣言幽远如山海之崇深,难以一二而推择,而贽之论,开卷了然,聚古今之精英,治乱之龟鉴。”南宋也有人把陆宣公的奏议进呈给皇帝,说:“斯皆治道之急务”,“无片言不合于理,靡一事或失于机,策之熟,见之明,若烛照”,希望皇帝把它“置坐之隅”,以引为鉴戒。直到明清,一些政治家对陆贽仍颂声不绝。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认为“唐室为之再安,皆敬舆悟主(陆贽别号)之功也”。尤其陆贽关于乏才七患、计听吏治、 核才取吏“三术”以及堵塞谏路“九弊”之论述,既是当时之细微观察,亦可为后世之明鉴。陆贽以“上不负天子,下不负所学”,以天下为己任,敢于矫正人君之失,揭露奸佞误国,其治国理政、以民为本的宝贵思想,无论置之于古今中外,只要统治阶层能够认真践行之,都会产生十分优异的效果。可惜的是,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,历代统治者或循于一家之私,或片面理解之,或怠于践行之,终无一例外地被淹没于历史的洪流中,成为中华历史的莫大遗憾。